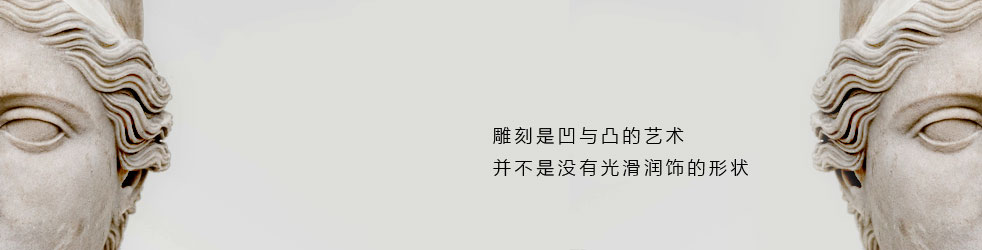
俞畅的成名作是他创作于1991年的《铁军》。
题材是革命的,反映的是北伐战争中叶挺的队伍,因为风格勇猛,所向披糜,当时被誉为“铁军”。俞畅取材就在这里。
雕塑的问题并不是写实,像模拟物体外表那样,在形体的起伏处行走。曾经有相当一段时间,我说的是西方写实主义进来中国,影响中国原有艺术之后,在雕塑领域,人们所理解的西化,表面看是写实,落实到塑造上,往往流于一种虚伪的真实。我稍微检索了近百年中国雕塑的发展,这样一种表面的模拟式写实,其实是很多雕塑家的追求。几代雕塑家在努力学习西方写实主义雕塑,尤其着迷于十九世纪末的罗丹,以为那样一种几乎乱真的手法,才是值得中国雕塑学习的对象。很长时间里,我们的美术史也一直把罗丹誉为“现实主义代表”,而忽略了其中的雕塑语言的独立意义。
为什么这样?也许还是摩尔说得对:“形盲的人多于色盲的人。”但摩尔的话需要解释,否则我们还是不能很好理解。在摩尔看来,“形”指什么?这一点很重要。他告诫我们,行走在河边时,捡一块河滩上的鹅卵石,把它握在手掌中,闭上眼睛,用触觉去体会自然在石头上做的功。那就是一种形,永恒而缓慢变化的自然所做的功,其中的规律,正是我们要深入领会的。摩尔接着说,如果想要知道什么叫形的自然变化,什么叫形的生长,可以把一块牛的腿骨握在手心,然后缓慢地从一头摸到另一头,在触觉里你就完全可以感受到其中的改变,里头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历史的丰满。
摩尔这些讲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话,其中对形的体会,我以为一直是这三十年中国有为的雕塑艺术家所追求的目标,更是俞畅从早年就开始的对雕塑有所悟道的内涵。把广东解放后的雕塑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各以一人为代表,也可以看出不同代际的雕塑家对形的认识。最早为广州城雕做出杰出贡献的广州雕塑院第一任院长尹积昌,他的《五羊》一经落成就马上成为了广州的符标,以至于其名声还远远超过雕塑家本人。在《五羊》中,尹积昌就在开始探讨一种更具概括力的雕塑语言。不过,从作品形式看,尹的追求多少滑向了某种装饰,用立面的图案化来作为对形的审美概括。这对于这样一座性质的城雕可能是适宜的。尹最重要的作品是原来立在海珠广场的《解放纪念碑》现已不存,置放在原地的同样主题的雕塑,是潘鹤和梁明诚在文革后重新制作的。不过,对比这两座同一主题的雕塑的形式感是一件有趣的事。尹的作品恰恰遵循了写实主义原则,有一种朴素感在,而潘梁作品则吸收了一种块面感,试图使解放军战士更具一种力量感。这恰恰也说明了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雕塑家们已经从某种朴素的形式感走到了形本身,而试图让形来独立说话,以达成审美目的。其实,年轻就获得巨大名声的潘鹤,他一开始进入雕塑界的其实是罗丹手法,在把塑造感转化为艺术语言的同时,保留了对对象的自由观感。他的成名作《艰苦岁月》,就多少让我们想起罗丹时代的那种浪漫情怀。
梁明诚作为比潘鹤更年轻的新一代雕塑家,幸运地在八十年代初到了意大利卡拉奇艺术学院进修。尽管只有短短的一年,但他在某种程度上却在这一年里把深入地体会了西方现代主义雕塑的发展历程,他巧妙地把摩尔的观点带回了中国,这一观点的本质是,强调形体的独立性,坚持用形,而不是所谓的表面真实来提升雕塑的艺术价值。而这恰恰也是俞畅的目标。对他来说,形甚至比符合物理起伏要求的真实更切合雕塑的需要。毕竟不是在模拟对象的外表,在三度空间里重塑物体的存在,而是让雕塑本身具有一种独立的穿透力,让作为雕塑语言的形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从某种程度上看,《铁军》恰是这一目标的一个结果,尽管题材是革命的,但那题材只是属于一个外在的表述引申而已。
从《铁军》来看,进入俞畅视野的,一开始就是对形的特殊处理。这里显示了他的聪慧与敏感,并不把对形的认识放在更本质地表达物体对外扩张这一方面,甚至,我怀疑他首先是从对形的处理入手,来解释他所要达成的革命内容。飞舞的战士那跃动的姿态是轻盈的,有一种不能自控的流畅在,而构成作品的细节,从身体构造到衣纹变化,再到手中的钢枪,却无一不是服从作者对形的规定的产物。不是由于对象本身的运动而让形发生了变化,而是形在独立地在发生作用,改变着形体原有的属性。具体来说就是,不是运动成为主题,而是形的飞扬让运动自觉地发生,并改变物体的可能属性,从而使作品具有真正的雕塑感。我以为这就是为什么《铁军》一出现就能捉住人们的眼光的缘故。专业界会毫无怀疑地认为,这是一件真正的雕塑,其激情正在于其中对形的独特理解与把握,而不是相反,仅只是一件以“铁军”为题材的简单创作。同理,蕴含在“铁军”中的那种英雄主义豪情也由此而获得了自身的意义,自由地述说着审美的价值。
其实,如果俞畅对摩尔所说的形有深刻认识,那么,他也就一定会像摩尔那样,用形的眼光来审视艺术史。在摩尔看来,正是罗丹那种表面模仿形体起伏,造成了雕塑意义的流失。他一再提醒我们,要注意罗马尼亚的布朗库西,正是他挽救了日渐衰落的西方雕塑。在摩尔看来,这一衰落正是由罗丹那种模拟物体外表而造成的。当然,摩尔的说法表明他对罗丹艺术的理解也并不完整。我的意思是说,不能把罗丹看成仅仅是依照物体起伏而工作的人,至少罗丹在雕塑中所表现的悲悯情怀,仍然属于人类艺术遗产的重要部分。但摩尔的意思却又是明白无误的,那就是,必须恢复雕塑家对于形的独立性的探索。正是布郎库西本人,尤其是他的作品《空中飞鸟》,通过对飞行轨迹的想象性塑造,通过对空气动感的形的寻觅,而让形从纷繁的物体束缚中脱颖而出,并成为自己。
同样的激情也一直贯注在俞畅的心中。《挑战》是结《铁军》之后的又一尝试,这一次俞畅以残疾运动员为对象,却探讨与《铁军》具有同样的形的独立性的问题。贯穿在《挑战》当中有一种流畅的气势,所有的形体都围绕着这一气势而呈现自身,从而让作品具有一种形的完整性。随后好几件作品,比如《男人》、《美体新模式》、《翔》、《追求》、《水上芭蕾》等等,都沿着《铁军》和《挑战》的路子,不断地探讨形的独立的可能性,以及这一独立性与所表达的主题的关系。其中也包含了俞畅作为雕塑家对人体与生命力的迷恋。《沉浅》和《失重》通过倒立的人体运动,让形与肌体合成整体。《清澈》、《铸》、《朝阳》、《天弦》是对青春的回忆与留恋,有一种低吟的况味在。《在水一方》和《山野》则是温和的,像是在探讨形体的独立性之余的习作,试图用一种朴素的手法回到形体本身,从而感受原初生命的温暖。有意思的是《取舍》,这件作品既表现了新生代对自我的关照,又把这关照与形体的切割结合了起来,暗喻着一种隐藏起来的消逝。而《原装》与《归真》则是同一作品的不同形式的呈现,表明作者即使面对同一对象,他的象征方向仍然会有不同的发展。作品的内核仍然是对形的分离,并通过这一分离来解释分别作为“原装”与“归真”的不同观感。
俞畅的探讨兴趣最后落脚在形的纯粹性上,这在他的《华丽的晶体》和《海鸣》这些近乎抽象的作品中可谓一目了然。尽管作品仍然有主题,但作者在这里显然只是借用而已。也就是说,俞畅的形变迫使他走到了几乎没有主题的领域,而尝试处理纯粹性与抽象性的关系,以及,就雕塑艺术而言,这一关系与形的走向的可能发展。也就是说,俞畅用自己近三十年的努力,完成了一个真正的形变过程,从对形体的物理属性的认知,到塑造形体与创作语言的关系,然后,让形独立出来,又不失其表达的力量感。他其实一直就在这些单纯的属于雕塑本体的概念中行走,从中试图雕塑出一个关于雕塑艺术的持续力量的前景。严格来说,俞畅的形变仍然在继续当中,他究竟有没有可能走向完全的抽象,这倒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始终用个人的创作,来为雕塑的独立性作有效的辩护。在俞畅看来,雕塑艺术的价值首先是对形的一种体察,然后,再用这一体察来落实对形的独特认识。这一认识过程,恰恰就是一个形变的过程。从这一点看,俞畅是一位真正的雕塑艺术家,他的努力,代表着眼下雕塑中人对这一古老艺术的全新思考。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副院士,博士生导师——杨小彦
发表评论
请登录